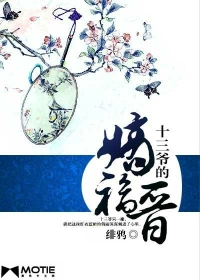“只是这件事如果出了纰漏,只怕到时候我们倒霉不说,可能还会连累到太子。”胤禛虽然这样说,但心里已经想着如何才能白胤禩一伙儿人埋进这个现成的坑里了。
胤祥倒是十分的不以为然,“四哥,你想的未免太多了些。太子爷得势的时候未见的多为咱们兄弟着想过,眼下他自己成了秋后的……”胤祥看着胤禛的脸色,咽下了后头半句话,心虚的摸了下鼻子,才继续说道,“再者说了,这事儿说到底最大的牵连就是你我了,若是我们不攀扯太子,他老八就是真的拿出什么‘证据’,没有人证。皇阿玛只要还念着仁孝皇后一星半点儿的,咱们的太子爷那就是稳坐钓鱼台的主儿。”
“这些话也是你可以胡乱攀扯的吗?”胤禛嗔道,“嘴上怎的连个把门的都没有?祸从口出,便是只有你我二人时也要小心才是,焉知隔墙有耳?”
胤祥索性自己倒了杯茶,灌了两口下去,“四哥也是谨慎惯了,竟是一点儿的松懈都不留。可若是如此,昨儿个晚上,您怎么没想到这一层呢?”
胤禛看着胤祥戏虐的样子,无奈的摇了摇头,“到底还是关己则乱。一时只想着要弥补你的疏漏,倒是忘了老八那头了。”
“依我看也未必都是坏事。”胤祥想了想,还是说出了口。“我昨儿就想过,他僧格找的这些番僧,若说是谋朝篡位的大事儿,都没说他有没有那个本事,您就先问问他有没有那个胆子。至于说是对付朝里的什么人,就这点儿歪门邪道的把式,也未免太不入流了些。”
“所以,你觉得他是要…….?”胤禛示意胤祥说下去。
“我有点怀疑他是打算替他那宝贝女儿出出气的。”胤祥把自己的推论说给了胤禛听,“如果这玩意放进我家里,把念声给害了,那他的女儿不就成了……”
胤禛听了一愣,随即表示不信,“不过是后宅妇人之间的龃龉,他僧格好歹也是朝廷命官,为了这点儿事儿就……”
“我起先也觉得不至于。”胤祥打断了胤禛的话,让他听自己分析完。“可是我又琢磨了一下,这些个不入流的手段,用在这种地方才最合适。您想,如果念声没了,他女儿是最有可能扶正的人选,毕竟你也说了,那是原本皇阿玛看中的人。如果没害到念声,也算是给富察氏出过气了,于他而言并没有什么损失。最后,如果事情真的败露了,他有大把的替罪羊可以用,他那原配夫人就是个不错的人选。我可听说了,僧格和现在这位富察夫人可是不睦已久了呢。”
胤禛吃惊的看了胤祥一眼,“刚还说你做事不够缜密,现在你就连这些个事儿都听说过了?”
胤祥在椅子上坐下,舒舒服服的翘起了二郎腿,“这叫什么事儿啊?平日里部里的应酬从不见你去,这些个花边儿新闻你自然是听不到的。若不是顾着官声,僧格只怕早就休妻另娶喽。”
胤禛苦笑着点点头,“行。就算你分析的有道理,跟咱们眼下又有何关系呢?我们的困局依旧是结局不定啊。”
“四哥,你怎么忘了谁跟老八是一头的呢?”胤祥坐起身子,靠近了胤禛两分,“老十四啊。”
“什么?”听见他提自己的亲弟弟,胤禛刚刚松动的眉头又皱紧了。
“若是这事儿真的关系到念声,老八那头难保不会查出头绪。”胤祥手指捻动几下,突然灵光一现,有了主意。“您说,如果让胤禵知道,八爷给僧格招募了这些个西域番僧,供他祸祸念声给他的宝贝女儿谋取个嫡福晋的位置。老十四会不会跟老八窝里斗起来?”
胤禛瞪得眼睛跟铜铃似的,好像从来不认识胤祥一般,把他上上下下打量了好几遍。“你……你这到底都是怎么想的?”旋即又说,“漫说能不能成,就是成了,胤禵他信了,可这里头的漏洞未免也太多了些,他只要稍作思量要拆穿此事根本不难。”
“那又如何?”胤祥已经把后续的问题思量好了,“所谓浑水摸鱼,就是要把水先搅浑了,才好下手不是?若是什么都板板正正的摊开来摆在明面上,那咱们哪儿有什么胜算?”
胤禛实在吃惊不小,胤祥的话让他一时有些难以消化。不过胤禛明白,不管走哪条路,都不能坐以待毙,随即也就有了主意。“一天,就一天的实际。我往海浩去试试,若是问出来了,咱们就走条最稳妥的路。若是真的问不出来……”
“若是真的问不出来,那就只能先下手为强,把水搅浑。”胤祥伸手冲下比划了一个搅和的动作。
既然事情有了进展和方向,兄弟俩的谈话总算是告一段落。
胤禛又叮嘱几句,便要回自己值房去。临到门边,忽又想起今早自家福晋的叮嘱,少不得站定了,问问大姐儿的情形。
“好得很。多亏了念声照料的周祥,这两天都好的差不多了。等着她大好了,我让念声带着她去给四嫂请安。”胤祥提起自家福晋,那叫一个骄傲。
胤禛瞅着他那傻笑的模样,很难把眼前这个“傻子”跟刚刚那个运筹帷幄的十三贝勒联系在一处。“也不急于一时,等着孩子都好了。我让你四嫂过去也是一样的。”说完也懒怠在搭理胤祥,背着手就走了。
海亮等着胤禛走远了,才敢溜边儿进了胤祥的值房,给人添茶倒水上点心。
胤祥已经打开了一本札子,头也不抬的没好气的说,“现在跑来献殷勤了?方才四爷在的时候,怎的连个影儿都不见你的?”
“爷,您是没瞧见啊。奴才看着四爷过来的是,那身上都带着煞气呢,就差旁边立块牌子了。”海亮把热茶放在胤祥手边,抱着条盘可怜巴巴的说。
“哦?什么牌子啊?”胤祥抬手示意海亮研磨。
海亮赶紧放下条盘,就打开了砚台。“生人勿近。”现在想想都觉得心有余悸,放砚台盖的时候手都是一抖,砚台盖在桌案上都磕出了动静。
引得胤祥白了他一眼,“那怎的?还放你半天自在,寻个地方躺躺,缓缓?”
“爷,您又打趣奴才。奴才歇了,谁伺候您啊?”海亮笑了看着胤祥,不耽搁把手里的东西摆好。“爷,您还真打算跟十四爷透那个信儿啊?”刚才胤禛在的时候,海亮只是猫在一旁,值房里的对话,他或多或少听见了些,再加上他对胤祥的了解,连蒙带猜的多少也能明白点胤祥的意图。
显然胤祥不是第一次跟海亮有这样的对话,也不甚在意,“那是迫不得已的法子。这里头毕竟还有念声的名节在,不到走投无路,爷也不想试。”
海亮听了不禁咋舌,这福晋在自家贝勒爷心里的地位真是非同一般啊,当年为着阿哥间的那些个事儿,自家主子可不是没动过把彼时已经怀了大姐儿那位舍出去的念头。想到这里,海亮便噤了声。
盐丁这几日俨然成了府里的新晋红人,别说是一般的下人们了,就是索多图见了他也少不了笑脸相迎。可日日跟在福晋身边,耳提面命的教训着,盐丁倒也不敢张狂,只是差事实在又多又杂,饶是他机灵,也忙的脚打后脑勺。
昨晚被胤祥耳提面命过后,念声倒乐的做个“甩手掌柜”,大大小小的事儿,只坐在自己院儿里等人来回,回的慢了,错了,也是不催不恼,与往日做派大有不同,连跟前伺候的小丫鬟都觉出了不对。
可念声就是打定了主意,任谁问都推说是自己这几日又忙又惊的,身上吃不消了,要将养些时日。至于挂蟾那边,除了让盐丁一天三次的跟花娘问过,念声自己连花房的边儿都没再沾过。
晚间胤祥回府,特意问了盐丁福晋在府里一天的事务,听完之后不觉有些奇怪。“就是如此?”他可从来不觉得念声会是如此听话驯服的人。
盐丁忙里忙外的一天了,晚间还要在主子跟前站规矩,就算吃不消,也还是强打精神回话。“贝勒爷,就是这些。福晋真的是哪儿都没去,就在自己院儿里,不对,是自己屋里呆了天。今儿连不是非回不可的事儿,都免了索多图进去呢。”
胤祥闻言略一沉吟,随即问道,“那福晋可传话说要我晚上不要过去了?或者让我自己用膳?睡书房?这之类的话说了吗?”
盐丁错愕的看着胤祥,“爷,您这是想什么呢?福晋刚下午吩咐厨房晚上烧了您爱吃的菜色,都让摆进她院里去了。您是不过去用晚膳了吗?”
胤祥摸了摸自己的下巴,总觉得哪儿不太对劲儿,可又说不出来,只好一扬手。“罢了。爷换身衣裳就过去。”只让盐丁先去知会一声。
这样“太平”的日子一共过了两天,到了第三天下午,十三贝勒府的门前,站了位贵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