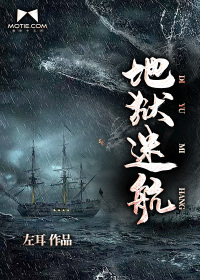侯聪是第二次来宇文府。因为侯家是主子。他到宇文府的重量,就相当于当今皇太子大驾光临去侯府。第一次的记忆完全模糊了——那是为了庆祝宇文府诞育男丁——长空。
宇文兴在正厅奉上茶,看着这个14岁的少年将军,老练中带着些阴沉,不急不缓地把早上进宫的事情说给自己听。他们两个的看法相同:当夜没有听见任何不寻常的声音,事后也不曾听见。是有人要借这个事关重大的预言,结合一个来历不明的女孩子,来祸祸侯家。所谓“调查”,查到什么不重要,只要开始查,就毕竟是人仰马翻。
侯聪喝了一口茶,侧耳听着外面的瑟瑟秋风,又转眼看着宇文兴:“但是,家宴上我和令媛比武的事是真的。也就是说,在皇上那里造谣的人,总归是来过宴席的人。这件事,我祖父不便出面,还要靠宇文将军。”
宇文兴心里,惊讶掺杂着欢喜。原来侯聪早已有了计划,并非要和自己商议,是直接来下命令的。这个杀伐决断的劲头,与他死了的父亲侯重,如出一辙;与侯老将军年轻时候,如出一辙。侯家,后继有人。
宇文兴话不多说,双目炯炯盯着小主人,双手拱了拱,表示听命。侯聪从座位上站起来,宇文兴带着默契,宣布送客。主宾走出房间,走到院子里,一路朝大门前行。秋风里,下人们跟在五六丈外,侯聪压低声音,把计划透给了宇文兴。接着,略微点点头,带着青松,在透天的菊花清香里,离开。
上轿子之前,他瞥见了牌坊上“画屏巷”三个字。长空那张猴子脸,顿时浮现在眼前。他曾在月色下叫嚣着,“白衣是画屏巷一霸”。“哼,到底是什么意思?”侯聪自言自语道,然后吩咐青松,“你别走了,留在这里调查一下。米糕留给你吃。”
青松接了这么个任务,想着厨房里新挑上来做羹汤的俏寡妇慧姐,还约着自己午饭后歇晌的时候过去,替她糊窗屉。一场美梦泡了汤,青松在巷口,掏出一块米糕塞进嘴里,笑不出来。
侯聪回了侯府,只见了祖母一面就回到了卧室。——祖父在营里忙着,并不在家,便是在家,他也不想透露任何信息。若要事成,必须机密。祖父会理解的。想到这里,他浴完了手,坐到床沿上。奶爸爸把那个傀儡人放在床头——“小白衣”,他叫了一声。越看越对自己的手艺满意,他找出最好的金绳拴好,另一头挂在自己手上。
一步一步,“小白衣”走动了起来。
“你觉不觉得,今晚会很热闹?”侯聪问。走到床的另一头的娃娃转身,笑得妩媚又亲切,点点头。
那一刹那,自从父母去世后的一切孤单,似乎都淡了。侯聪把金绳细细系成蝴蝶结,服帖在娃娃的背上,这样就不会乱。然后,他将“小白衣”搂进怀里。他保持这个姿势,吃了新来的俏寡妇厨娘做的羹汤和肉饼,踏踏实实睡了个午觉。
华灯初上。宇文府上,颇为热闹。侯崇底下最嫡系的将军、校尉们,齐聚一堂。帖子是下午发出的,理由是庆贺白衣成为大公子的挂名奴。其实谁都知道,这就是同侪之间叙旧交流的借口。人来的比中秋夜还齐全,后花园面西的画堂二楼上,灯烛辉煌,觥筹交错,热闹非凡。一道道热汤菜被奉上,这些刀口舔血的汉子们渐渐放松,说着些琐碎的事情,深宅奇闻,青楼轶事,渐渐地,酒过三巡,陷入微醺。
宇文兴坐的主位,身后直接连着一个密室。侯聪,背着手,由青松陪着,通过风眼儿看着这一切。他敲了敲密室的窗,给了宇文兴一个信号。宇文兴得令,收起笑意,扫视了一遍画堂,陡然起了一个新的话题:“我听说,在座的,有人在外头胡说,告诉旁人——中秋夜老将军家宴上,我家白衣与大公子比试的时候,起了龙吟声。这话啊,长了翅膀,都传到宫里边去了。是谁这么莽撞,我宇文家不要命的吗?”
话音刚落,席间就站起了三个人。这三个人,分别是镶紫将军独孤演、振声将军元贺、承华将军慕容立。中秋夜,独孤演在押粮进京的路上,元贺当值负责城防,慕容立家小妾生产,都请了假,未曾出席。他们三个人听了宇文兴的话,纷纷表示与自己无关,而且极度气愤,要求查个清楚。
独孤演紧盯着斜对面的郑将军,声音洪亮,“查不清楚的话,谁都不许走!这玩意儿没跑,就是在座的惹的事!”
“对,”元贺附和,“咱们从军多年,还不明白这种道理吗?这种话能乱说吗?一旦闹大了,主子的前程,加上我们所有人一家大小的脑袋,还想留着吗?”
郑将军拍了拍桌子,反咬独孤演,“你看我干嘛?查就查,谁怕谁?我同意,查不出来谁都不许走。包括你们三个!哼,人不在场,就没有嫌疑吗?”
郑将军的话说完,获得了全场的赞同。侯聪在密室里终于露出了笑意。到这一步,他的计划才算成功了。这座建筑本来是为了观花而造,如今,一楼被封得死死的,所有将军、校尉跟来的侍从,都被让到偏院吃喝嫖赌去了,没有传递消息和串供的可能。如果一切顺利,不仅能查出谁在外面故意造谣,还能趁机观察一下这些人私底下真正的关系,还能察觉一些连祖父都不知道的惊心动魄的、大大小小的阴暗与灰尘。
侯聪的手轻轻伸出来,接过了青松捧了好久的甜酒,边喝边看戏。他看着一切顺利,觉得在密室里困得久了,有些乏味。这画堂二楼主要是个大厅,其中一侧对着花园鱼池,另外三面围着游廊,侯聪小心翼翼从密室出来,青松跟在后面,由着他在游廊上轻轻走动,随时听着里面的进程,留意戏演到了哪里。
外头的侯聪使了计策,里头又何尝不是一窝人精,在保全自己与真正好友的同时,往死里挖掘。三刻钟不到,水落石出——护泉校尉夏怡,与另一位大柱国将军常赢手下的范姓将军有偏亲,二人在中秋后的第二天一起喝酒,夏怡说了宴会上比武的事儿。“并非故意”,但是太过惊讶于白衣的武功,引用了“龙吟处处月照花”的预言,竟然被姓范的出去传成这样。
宇文兴站在夏怡面前,其他人站在他身后,怒气冲冲。
“老夏,这就是你不懂事了。侯府上发生的任何事,哪怕是猫捉耗子这种司空见惯的景象,不管你我中的谁看见了,也一个字也不许出去说。你说便说了,还说给常家手下的人听;不仅如此,刚才我们既然提到,你就该自己招了,结果……”
宇文兴停顿了一下,独孤演接上,“先捆起来,现在就派人去上报侯老将军,罚他!”
“不,”宇文兴按照侯聪的计划,执行得滴水不露。“今日酒宴,是为了我家小女做大公子的挂名奴,是为了白衣的荣耀,和大公子的康健,诸位是作为孩子们的叔叔伯伯来的。刚才发生的一切,还是老规矩,一个字都不往外说。怎么样?”
侯聪已经下了楼,藏身在不远处的花丛,看着宇文兴打开了画堂大门,开始送客。忽然觉得左边耳朵一热——他扭头望去,只见昏暗里一个捕捉了他一瞬魂魄的娇俏影子刹那滑走,等他定睛观察,只见到宇文长空咧着嘴站在不远处,后面六个奶妈子跟着。从影子来看,长空高高的个子,正好挡住了一个人——白衣那个死丫头。
“你们在这里干嘛?”侯聪皱着眉头。
“我爹爹吩咐的,来跟大公子学点儿心眼子,将来为大公子效忠。”长空的心情非常好。
“滚吧,我不想看见你们。”
“遵命。”长空说完,面对着侯聪开始往后退去。“大公子,别怪小的不能转身。这一转身啊,你最怕看到的人就露出来了。”
话虽然这么说,其实长空不是怕露出白衣,是为了自己能对着侯聪,多做几个气人的鬼脸。
但侯聪根本没看他的脸,他的目光追随的是那个易碎的影子,白衣的影子。瑟瑟秋风,月光与烛光交映,地面竟然起伏着涟漪。是错觉吗?或许是吧。他分不清哪一部分影子是她的。
两个人就这样见了“一面”。差点就是“最后一面”。
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