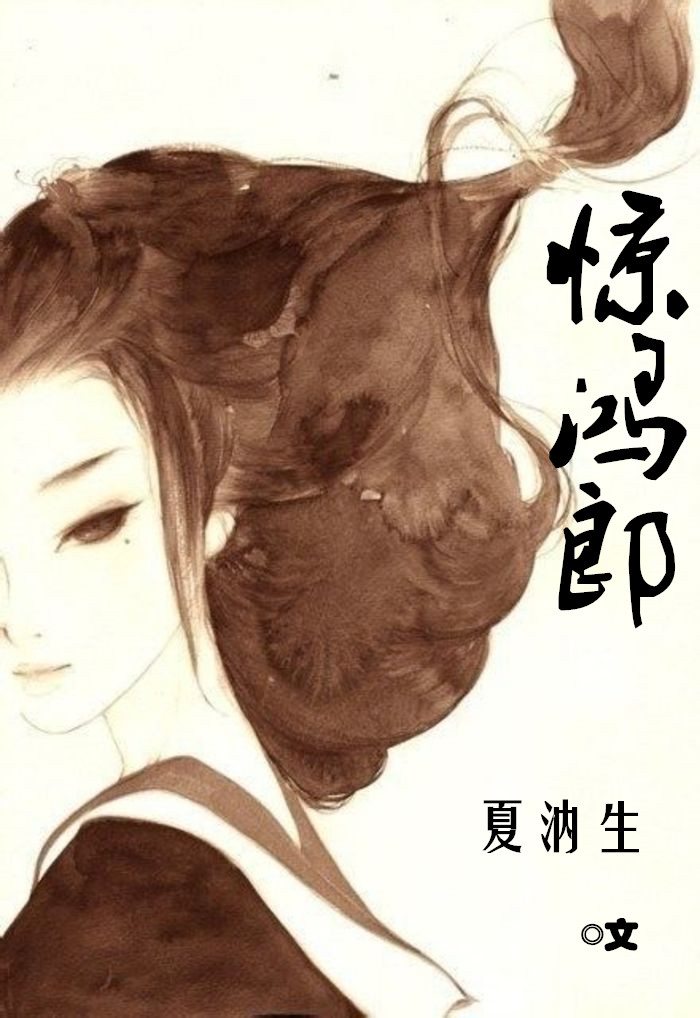正值隆冬,新鲜蔬果紧缺,再加上惊鸿山庄地处偏远,郎徒们不得随意出庄下山,所以山庄内特有菜窖二三,用来保存大量蔬果,可供山庄内三月不断口粮。
菜窖上有一小口,铁门从外拴紧,小口仅容一人出入,每日取菜时登梯上下。
今日伙食由玄武上房负责,众郎徒一律表示很担忧,提前做好挨饿的准备,也做好无论多么难以下咽都要抚掌违心称赞的准备。
清晨,天刚蒙蒙亮,范流棋就将其余四个睡得屁是屁鼾是鼾的大男人强行从温暖的被窝拉起来,浩浩荡荡向膳房进发。
施易一直到站在灶台前,才把迷迷瞪瞪的睡眼彻底睁开,满脸难以置信地瞪着手中的铜勺,作势挥了挥,不解地朝颜昔道:“这是在……让小爷我颠勺?”
颜昔坐在灶前打着火石,看起来摩擦地颇为费力,白皙的脸上微微泛红,“唔,范小侯安排的,你掌勺,我烧锅,花少淘米洗菜。”
“我们为什么要听他的?”施易叉腰干瞪着着眼。
颜昔手下一顿,迷惑地抬起头。是啊,我们为什么听他的?
“还有,他跟云凛跑哪儿去了?”把我们支使得团团转,他自己撂挑子走人了?
“去菜窖搬菜去了。”花容哆嗦着从屋外进来,甩着通红的手,哈气道:“施小爷,你要是嫌弃,要不咱们换一下?这水委实太冷,淘个米一双手就没知觉了。”
“滚滚滚,小爷我还是颠勺吧。”施易新奇地舀着大锅里的水,颇有兴致。
范流棋本来想从旁指挥一下施易的,毕竟五个人里就她还算有一些烹饪的常识。小时候在侯府,她时常在膳房给母亲煎药,婆子们忙活的时候,会让她打打下手,她虽然没亲自上过灶台,可没吃过猪肉见过猪跑啊,怎么也比那些娇生惯养的少爷们强一些。
可不知怎的,偏偏被云凛拉着一道去菜窖。
也不知当初建菜窖的人是有脑子有疾还是怎么的,把菜窖建的离膳房那么远,一路上云凛自顾自地走着,半句话没有,沉默把本就有些远的路途拉得更远了。
范流棋背着硕大一个菜篓子,嘟嘟囔囔了半途,突然撞上前方猛然止步的背影,撞得她眼冒金星,吃痛地捂着鼻子。
云凛转过身,无奈地道:“你在嘀咕什么?”
范流棋摇摇头,只觉得掌心一片不同寻常的温热,摊开一看,赫然满手心的鲜血……这是被撞出鼻血来了?范流棋苦笑着仰起头,许是天气太干燥了些吧……
云凛一看见了血,心下有些慌乱,他这才想起范小侯自小疾病缠身,羸弱异常,这几天相处下来,看范小侯活蹦乱跳完全半点没有病秧子药罐子的迹象,他几乎以为那纯粹是外界谣传了。这会儿,莫不是病发了吧?
他忙从袖口掏出一方手帕,手忙脚乱地替范小侯擦拭汹涌而出的鼻血,手帕上一股淡淡的檀香飘进鼻子,范流棋用手捂住,瞧见帕子一个角落上绣着一株淡紫色鸢尾,娟秀精致,恬静淡雅。
“多谢殿下,流点鼻血而已,冬日常事,无妨。”她捂着鼻子闷声道。
云凛嫌恶地瞥了他一眼,“听闻你久病,怎么这些日子没见你服药?”
范流棋讪讪笑了两声道:“是药三分毒,平时喝得够多了,不差这一时半会儿。”心里暗道:看来下次下山探亲,她得抓几副滋补的药方来煎着喝,免得遭人疑心。
两人行至菜窖口,范流棋的鼻血也止了,她暗搓搓地把手帕塞进怀中,恭敬道:“殿下的帕子,我洗净后再还给您。”
“不用还了。”云凛摆摆手。
“可是……”看上去似乎是女子所赠的信物……就这么不还,不太好吧?范流棋看了眼面色不虞的云凛,把下半句话吞了回去。
云凛用钥匙打开铁门上缠着的锁,身子往里探了探,里头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他皱了皱眉头,自怀中掏出一只火折子,吹燃,猫着腰先进了里。范流棋随后跟上。
菜窖里逼仄昏暗异常,门口一丝光线照进来,隐约视物,窖里散发着各种白菜秧子葱蒜味,气味浓郁,呛得范流棋顺着阶梯一下来,就打了个震天响的喷嚏。
还想继续打第二个,被云凛阴鹜嫌弃的眼神给生生逼了回去,逼得她眼泪都出来了。
“把菜装进背篓里,快点出去。”云凛举着火折子颐指气使道,一张脸黑得不能更黑。
七皇子今日心情似乎特别不好……范流棋暗暗翻了个白眼,不与他计较,取下背后的背篓,开始往里捡菜。大白菜、芋头、莲藕、荸荠……正当她认真思虑着该如何配菜的空档,头顶突然传来一阵异常的铁链窸窣声。
心头陡然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她猛地回头,对上云凛同样惊疑的眼神。云凛反应极快,拔腿就顺着阶梯奔上去,未及到门口,铁门便砰地一声关上了,随即便是缠铁链咔哒落锁的声响。
云凛发狠猛踹了一把铁门,把铁门踹得嘎吱直响,门外的人显然动作还没快到瞬间落锁,死死抵着铁门。
“放肆!门外是谁?”云凛往外推门,与之僵持不下。
门外人闷不做声,一阵角力后干脆利落地落了锁。
云凛做了一系列尝试后,撞也装了,撬也撬了,确定推不开铁门,阴沉着脸下来了,一下来,范小侯便凑到他的手边。
“别!”
云凛还未来得及出声阻止,范小侯就眼疾手快地吹熄了火折子。
“我们眼下被困在这里,只能等人来救。地窖里空气不足,待久了易缺氧窒息而亡。火折子燃烧会消耗所剩不多的空气,灭了好。”范流棋自顾自冷声解释道,完全没察觉到身旁人的异样。
等她在黑暗中从被困的慌张中冷静下来后,她才注意到翎王殿下自方才熄了火折子之后就一声没吭过了。
“殿下?”她轻轻唤了一声。
回答她的是一连串时急时缓的粗重喘息声,她凝神倾听,越听越心惊。
“云凛!”她连忙扑过去,摸到不知何时蜷缩起身子,窝在角落里的云凛。
范流棋刚缓过来的心跳一下子又蹦到嗓子眼,她在黑暗中摸索到云凛颤抖冰凉的手,顺着手臂摸到他的脸上,摸到额上一脑门的冷汗,心下大骇,有些语无伦次:“你……你怎么了?”
“光……光……”云凛断断续续艰难地吐着字。
范流棋把耳朵凑近他唇边,温热的气息扑在她耳垂上,她听清了云凛说的话,连忙把他手里紧紧攥着的火折子拿出来吹燃。
菜窖升起如豆般微弱的火光,也照亮了云凛苍白得骇人的面孔,额上一片晶莹的冷汗,顺着额角滴落,在这冬日里显得尤为突兀。他的嘴唇微微干裂颤抖着,大口大口地吸气吐气,胸膛也随之剧烈起伏。
范流棋举着火折子靠近他,面色复杂,这是……什么病症?
“别熄,我宁愿窒息死。”云凛抬起乌黑的眸子,瞳孔里跳跃着火折子的点点火光,他死死盯着范流棋手中的火折子,不错眼珠,里面一片空洞,像是一个没有生气任人摆布的傀儡。
范流棋靠近他,挨着他肩膀坐下。
“殿下……你这病……”范流棋斟酌着用词,刚想开口询问,身侧的人头一歪,枕在她肩膀上不动了。
范流棋仿佛瞬间被下了定身咒,不敢动弹分毫,举着火折子的手有些发酸,可又不敢落下来。
“这病,治不了。”肩上的人虚弱地开口,声音像是刚采摘的棉花,软绵绵的,透着无力,气息吐在她的锁骨处,微微发痒。范流棋不自然地扭了扭身子。觉得,现在的七皇子才像是盛传的草包皇子,而不是那个敢下湖救人,能一手掰断别人骨头,一个眼神就能让全场噤声的修罗。
“不试试,怎知治不治得好?”范流棋宽慰道,想想她大哥,旁人都道他病入膏肓回天乏术,他不也依旧顽强地撑着吗?以后肯定也活得比那些迂腐老头子预料的都要长久。
云凛沉默了一会儿,拉过她未拿火折子的那只手,范流棋下意识想缩回,可考虑到他现在可能神志都不清了,便放弃了挣扎,由着他将她的手拉到他胸口,停在心脏的位置。
范流棋能感觉到掌心下的胸膛,在强有力地震动。
“这里的病,要如何治?”云凛转过头,扯出一个苍白自嘲的笑。
微光下的那张俊美无俦的脸,令范流棋的心跳猛地漏了一拍。
<更新更快就在笔趣网www.biquw.com>